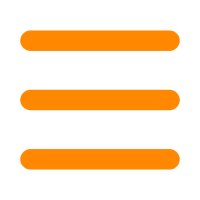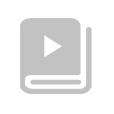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保护一直以来都是以国家为视角,忽视了社会的救助用途。在社区矫正兴起以来,社会的帮扶用途日益得到看重。本文立足于社会角度,期望可以构建一个社会对被害人的救助保障体系。
社会 被害人 精神抚慰。
伴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生,各国对于被害人开始直接而全方位的保护。第一,打造了国家补偿规范,对于那些因犯罪行为而受重伤或者死亡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予以资金补偿;第二,打造了相应的被害人援助规范,从提供法律建议、心理慰藉、经济援助等方面保护被害人;第三,刑事诉讼当中也重视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增加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其中,对于被害人在受侵害后的社会救助与抚慰尚付阙如,亟待一套完备的体系帮助被害人更好的恢复。
1、社会对被害人救助有哪些用途。
社会对被害人的救助主要体目前防止被害人遭到“二次侵害”。二次侵害是指“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是首次被害,犯罪之后因为社会的歧视、忽略与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由于不当刑事司法行为所遭受的侵害是第二次被害。”i在现实日常,被害人一般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惩治罪犯,获得经济赔偿,但其却不可以因此得到彻底解脱,被害人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封闭心理倾向,强迫自己与社会生活离别。精神病心理学家桑德拉·布鲁姆在其《避难所的建造》一书中指出:尚未治愈的精神创伤易于被激起。假如没对精神创伤加以妥善的处置,在历程此创伤的人、家庭甚至其后代的日常,这类精神创伤都会被激起ii。精神创伤不止是被害人的核心历程,而且也是很多加害人的历程。很多暴力事件的发生,事实上是先前历程了精神创伤而该创伤又没加以妥善地对待,由此重新被激起。因此,恢复精神创伤对被害人来讲是要紧的。
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主要表目前职权性、物质补偿性、条件性。第一、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依职权所作出的,该行为具备合法性无疑但欠缺合理性。对于已经受伤的被害人更需要社会中有爱心的群体给予温和的、适合的帮忙与救济。第二,国家对被害人的抚慰与救济是以惩罚犯罪、给予被害人补偿金达成的,而对于被害人精神上的伤口却没办法安抚,也没办法帮助其更快的恢复与融入。在此,社会的功能则能更好的体现,尤其是在帮助被害人弥补精神创伤、融入社会方面。最后,国家对任何救助行为都有严格的规定,符合肯定条件和标准方能作出,也就是说,有不少被害人会由于救助标准的不合理而得不到救助。由于有些被害人虽然遭受的犯罪侵害较轻,但导致的伤害却非常重,因为国家的严格规定,不可以法外施恩。
因此,从上看出大家绝不可以忽略社会对被害人恢复方面有哪些用途,它是国家这个主体没办法替代的,在救助方面具备人性化、温和化、全方位化的特征。
2、构建被害人社会救助保障体系。
《刑法》(修正案八)推行以来,对犯罪人社区矫正已经陆续在国内展开,社会的矫正与救助用途得到认同。打造对被害人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已经势在必行。这个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造被害人服务机构。国内尚无被害人援助机构,考虑到国内现在庞大的被害人队伍,这种机构非常有打造的必要。同时这类机构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iii。可以参考受侵害的犯罪类型不同,组建不一样的服务机构,比如性犯罪被害人服务机构、未成年人被害人服务机构与被拐卖妇女儿童亲属的服务机构等。
第二,提供特殊的医疗服务。因为社会中存在对犯罪事件的反感,使得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人,都存在一定量的受歧视现象,因此被害人常常得不到应有些同情和应有些治疗或在医药成本上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如此不但被害人的伤情得不到有效治疗,其心理还会遭到进一步的创伤。因此,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职员对待被害人应比普通的患者要看重。
第三,提供有效的经济援助。被害人受害之后,因为忽然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或因治疗身体遭受重大损伤而支付巨额医疗费,总是在经济上会遇见困境,虽然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被告人赔偿和国家赔偿,但因为具备滞后性且数目有限,远远难以满足其需要,大家应通过保险赔偿、社会援助、社会捐助等渠道对其给予适合的经济援助。这种经济援助是很必要的,是社会救助对国家救助的必要补充。由于国家只有在判处被告人有罪后才能启动附带民事诉讼和国家赔偿,而在之前的一段诉讼关键时刻却得不到物质补偿,这是非常大的漏洞。
同时,应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应当在被害人受害之后准时向他们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消除和缓解被害人所受的心理损害,被害人的亲友、邻居、同事、刑事司法职员、医疗职员和别的人员及大众媒体应付被害人的被害历程表示理解与同情,不可以对其进行歧视,而应向其提供感情上的支持。尽可能发挥社区的矫正、修复功能,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修复被害人的损失。
最后,尊重被害人的人格。应付司法职员、医疗保健职员、自愿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及其其他有关职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受害者心理健康的需要,对受害者不应抱有轻蔑甚至是指责的态度。对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件不应传播,并限制大众媒体公开报道。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动员社会力量为被害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忙,包含生活、就业等方面,以促进被害每人格尊严的恢复,使其重归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对被害人的保障体系并不可以代替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规范,国家仍然是主导。只有国家以其强制力为保障,才能达成惩罚犯罪、追索赔偿金,即“矫正的正义”。而且社会救助体系应当形成与国家救助规范合适套的补充体系,互通有无、信息共享,从而打造一个包容、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冯卫国著。《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陈彬,李昌林。论打造刑事被害人救助规范[J].政法平台,2008年4月。
注解。
1参见刘会平,《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硕士毕业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十月。
2霍华德·泽赫。恢复性司法[A].狄小华,李志刚。刑事司法前沿问题——恢复性司法研究[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
3参见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69页。